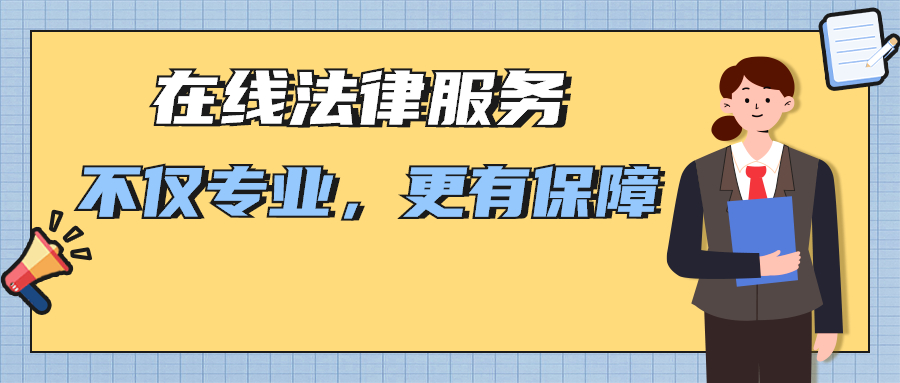一个洗头妹眼中的法治世界
近十年,我都在家附近的一家美发店打理头发,我长年直发,既不电发,也不染发,有时候剪剪,有时候洗洗。店主是个年轻的小伙子,三十岁不到,却是我来这家店他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。洗发的小工倒是常换,但唯一的女工,有三四年了,一直留在这。她矮矮的,胖胖的,大约才到我的肩膀。我并没有仔细的打量过她,每次一进到店里,说洗头她便跟在身后。洗头在这种高层商铺的二楼,日常的光线并不明亮,顺着她指的位置躺下来,水缓缓地流在头发上,我并看不到她的模样。
她很喜欢说话,经常推荐我搞各种各样的洗头产品,我并不待见这种推销方式,有时含糊,有时假寐。一来二去,她便也放弃了,但话来是要说的。什么吃饭了没,你住在附近吗,在哪上班呢。我对此类问题敏感而又抵触,总是以抽象概念来回应。她似乎听不出来,下次来还会问。直到有一次,带女儿去理发,同样的问题,女儿一股脑说了个透彻。我对女儿的实话实说有点恼火,但又不知该怎么和孩子解释说,我们此处应该撒谎,又为什么要撒谎。
那次之后,她便与我熟络起来,长时间不去,她还会问我工作是不是很忙。我并无心与她走近,每次只是客套两句。只是在洗头的时候,她还会唠叨,东拉西扯,终于有一天,她问我,如果被人告到法院该怎么办。
是啊,这个问题问一个法官,不变的答案,都是积极应诉啊,有条件请个律师,没条件就自己去,把知道的都和法官说一说,你如果有道理,法官也不会冤枉你的。
“我没有钱,也请不起律师,反正也不关我的事,我弟弟让我签个字,我就签了个字,其他我什么也不知道,他们爱怎么告就怎么告。”
这种语言如果在法庭上,不会给他们说第二遍,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意义。签字是个极其重要的法律行为,肯定很简单,但要想否定却没那么容易。
我不知道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会变得更奋发图强,还是会更肆无忌惮,不过,我觉得后者可能更多。“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”似乎在这里都反了。
她继续讲,整个事情的前后。原来是她的弟弟用她按揭的小房子去办了抵押,现在被银行告了还款。那房子又小,也不在城区,但话里话外,应该是她唯一的大宗财产,而且还有个小女儿也和她一起生活。她没有我想像的害怕与窘迫,甚至我和她提及不能还款可能房子会被收走,她也无所谓。大约是自己只付了一点首期,也没供多少,收走了也就损失了首期,大不了带着女儿租个房住。
不同的生活境遇,不同的职业选择,让我们对同样一件事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。她没有再说细节,我也没有再追问。他们的世界有着我们不能解决的矛盾和困境,我们的语言同样也有他们不能明白和理解的认知。就像一场措手不及的大雨,她身陷雨中,需要的只是撑伞的人,而我们不是,只能配合一种听雨的心情罢了。
这件事过去很久,她都没再谈起和房子有关的事情。偶尔遇到,有一搭没一搭聊天,就像热闹都市里孤寂的灵魂,因为陌生,才显得真实,说完也就散了。
今天,我又去剪发,二楼昏黄的灯光,照例是水温温地洒在头上。她胖胖的手指熟练地搓出白色的泡沫。我想像着头发在她手中的样子,她终日对着顾客的头顶,会不会像我们看到案卷一样,也会厌烦吧。
她的开场白,总是会说,用什么洗发水,然后就是,你有点掉头发。我的回应也永远是那几句,普通的就好,是的,有点掉。
弗洛伊德说,人可以防御他人的攻击,但对他人的赞美却无能为力。
洗头小妹以实际语言践行了这句话。她对我的职业给予了高度评价之后,又极其诚恳地和我说:你是法官哦,我这个问题问你,你肯定是懂的。
应该懂吧,我心里想,她只要不是问我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为啥不进民法典就行了。
或许是有些不好意思,她问了一个并没有交待主角的问题。
“一个人如果被判了十年牢,那他什么时候能被放出来?”
“十年啊,那估计得坐八九年了。”
“但是他去年就被抓进去了,已经被关了一年多了。”
“那就从被抓那算十年。”
“如果表现好,会被减刑吗?”
“正常应该会的,不过不会减很多的。”
“罚金必须要交吗?”
“最好交吧,应该会对减刑有帮助。”
“坐监以后,家里人能去看吗?”
“可以,有固定时间,可以探监,也可以送点生活必需品。”
“那可以送吃的吗,火腿肠、感冒药之类的。”
“这个得具体问问监狱,药估计不行,万一你把其他的药放进感冒药里呢。”
“哦,那也是,可生病怎么办好?”
“监狱里有医生,小病没事,大病会通知家属的,放心吧。”
短暂的沉默,我没有追问是谁坐监狱,但肯定和她关系密切。没有人会对这些负面的生活感兴趣,就像一种疾病,如果和自己无关,也没有了解的欲望。
可是,她叹了一口气,说道,“我弟弟,你知道吧,就是我之前和你说过那个房子的事,我弟弟,诈骗,被你们法院判了十年。”
我一下警觉起来,“是我们法院吗?”
“不是,不是,是在东莞第X法院。你们不都是法院的嘛。”
天下法院是一家,确实如此。
“那现在去哪个监狱服刑了?”其实问这个问题纯粹躺在洗头床上的下意识,好像脱口就说了,并没有想知道的目的。
“还不知道,昨天刚判的。”她的手还在我头上挠着,不知道她的表情,语境平缓地没有变化。
“那你们还上诉吗,如果觉得判多了,可以上诉试试。”很无用的安抚话,我又加了一句“上诉不会加重的,最多还是十年。”
“律师说了,用处不大。”
“试试看嘛,万一能减点呢。”
“算了,上诉那个律师还要再收两万块。”
“哦”,我应了一声,没有再建议她,那是他们的两万块,他们会像我们统计收结比一样计算出一个百分数,然后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,毕竟用钱争取的自由与捍卫的权利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
又是很短时间的冷场,似乎又没有找到新的话题。在一个家里有人坐监狱的听众面前再谈法律似乎有点不合时宜,毕竟我们信奉的,是他们破坏的,我们遵守的,是他们违反的。
“那我弟坐牢了,我女儿是不是以后就不能考公务员之类的了。”
她问出这个问题来,多少让我有点吃惊。一来是吃惊于她竟然了解这样的政策,二来说明她至少有这样的想法,没有在这种乱七八糟的细节中沉沦下去,从根本上忘记这种生活需要改进。
“父母可能会有点影响,但舅舅可能关系不大。再说了,不当公务员可以去当医生啊、画家啊、建筑师啊,有文化怕什么。”
“也是,我就想我女儿多读点书。”
“是的,女孩子还是要多读书,读书是最好的出路。”
我不知道向她说出这样的话来,到底能有几分的作用与意义,但是我就是挺想说的,我甚至有一瞬间的冲动想坐起来和她长谈一下,语重心长地告诉她:当生活是一地鸡毛的时候,慢慢地把它捡起来,然后鞭策自己,总会越来越好。

可是,我没有,我最终选择尊重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。
她三十三岁,可是我认为她长得大约像四十五岁。
她的弟弟二十八岁,骗了别人七八十万,还有十年被禁锢的时光需要渡过。
她有两个姐姐、两个弟弟,她的父亲“脾气暴躁,又很窝囊没本事,遇到事情总让女人出头”。
她未婚先孕,有一个读低年级的女儿,男人有家庭,但是她说从不后悔跟了这个男人,现在这个人偶尔也帮她带孩子。
她每天骑电瓶车大约四十分钟来这里上班,孩子放学就在托管那里,直到她晚上回家。
她的房子月供1700,没有断供,但是之前的案件,还没有人执行这个房子,她说月供就当租房的钱了。
她讲完这一切,我说,你不怕等你供完了房子,被银行拿走吗?
她说:法律也要讲人情吧,我孤儿寡母的,就这一个房子,你说是吧,法官,法律是要讲人情的吧!”
头发洗好了,我起身笑了笑,没有回答她,我正面看了看她,发现她头发有点自来卷,稀稀地、蓬松着,皮肤不是太好,手白白的,一只眼睛有点斜视。